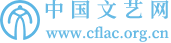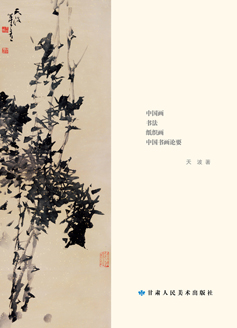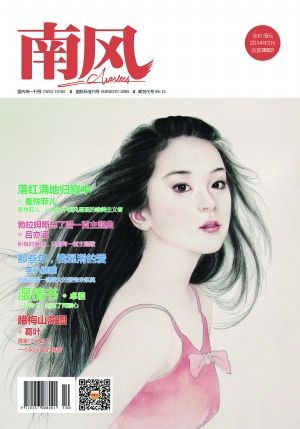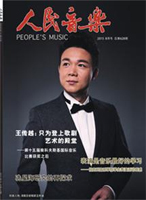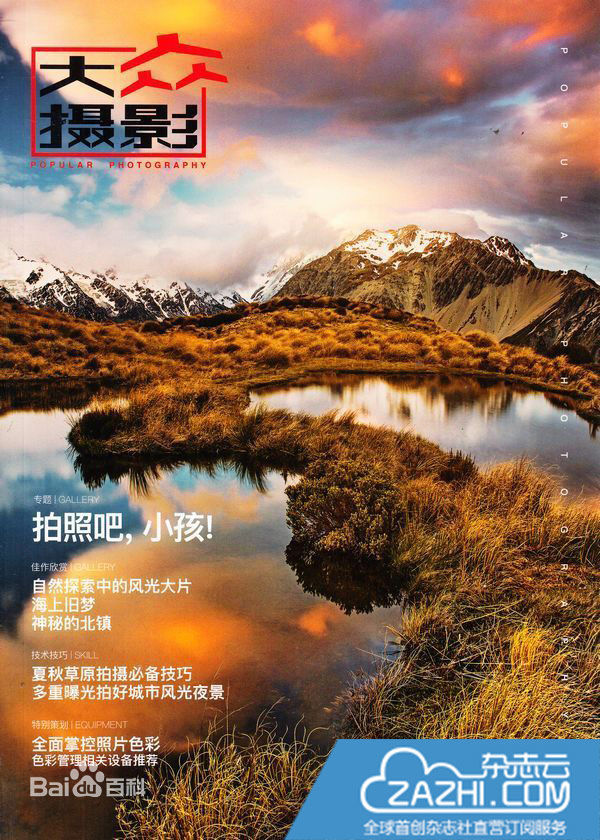◎ 正是因?yàn)橛跋窦夹g(shù)的出現(xiàn),我們才能夠比較確切地記錄人類社會(huì)與文化的許多真實(shí)圖景,這也使得20世紀(jì)成為第一個(gè)“寫真”的人類百年史。
◎ 影像民族志工作者反對(duì)這種對(duì)影像權(quán)力的濫用,更反對(duì)將自身的文化意志凌駕于研究或拍攝對(duì)象之上,更不能通過(guò)擺拍、虛構(gòu)或拼湊素材等方法,炮制符合自身需求的影像文本。
◎ 從已經(jīng)完成且公映的多部村民影像作品中,我們能夠看到許多有別于主流價(jià)值與外部視角的民間文化觀念,它們以影像為載體,對(duì)本民族或本社區(qū)的鄉(xiāng)土知識(shí)進(jìn)行了“主位”立場(chǎng)的文化表述。

青海果洛藏族聚居區(qū)的牧民在練習(xí)影像拍攝技術(shù)

本文作者在四川理塘藏族聚居區(qū)進(jìn)行影像民族志拍攝
近半個(gè)世紀(jì)以來(lái)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的劇烈變遷,令傳統(tǒng)的民間文化出現(xiàn)了嚴(yán)重的存續(xù)危機(jī)。無(wú)可逆阻的全球化、城市化與工業(yè)化進(jìn)程,將鄉(xiāng)村和集鎮(zhèn)千百年積淀的民間文化水土迅速?zèng)_刷,以農(nóng)民和手工業(yè)者為主體的民間文化傳承者,也面臨著后繼無(wú)人、技藝絕嗣的消亡命運(yùn)。在這個(gè)歷史性的社會(huì)發(fā)展時(shí)期,中國(guó)民間文化保護(hù)事業(yè)既面臨危重的困局,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國(guó)際社會(huì)關(guān)注、國(guó)內(nèi)政策支持以及新技術(shù)、新媒體優(yōu)勢(shì)。特別是數(shù)字影像技術(shù)的迅猛發(fā)展,為民間文化的保護(hù)與傳承提供了新鮮而澎湃的動(dòng)力。
以影像方式保存民間文化,并非是一種新奇的方法。自從靜態(tài)攝影(照相)與動(dòng)態(tài)攝影(電影)在19世紀(jì)先后問(wèn)世以來(lái),很多國(guó)家的博物館、學(xué)術(shù)機(jī)構(gòu)或文化組織便紛紛采用拍攝照片或影視紀(jì)錄片等方式,對(duì)于瀕臨消失的文化現(xiàn)象進(jìn)行影像記錄。這些影像制品,因其相對(duì)逼真地保存了某些民間文化內(nèi)容,也成為后人欣賞、學(xué)習(xí)甚至“復(fù)原”傳統(tǒng)文化的參考資料。可以說(shuō),正是因?yàn)橛跋窦夹g(shù)的出現(xiàn),我們才能夠比較確切地記錄人類社會(huì)與文化的許多真實(shí)圖景,這也使得20世紀(jì)成為第一個(gè)“寫真”的人類百年史。進(jìn)入新世紀(jì)之后,以影像生產(chǎn)和消費(fèi)為主體的視覺(jué)文化更是進(jìn)入了空前繁榮的時(shí)期,正如著名學(xué)者周憲所言:“視覺(jué)因素一躍成為當(dāng)代文化的核心要素,成為創(chuàng)造、表征和傳遞意義的重要手段。在比較的意義上,我們今天越來(lái)越多地受到視覺(jué)媒介的支配,我們的世界觀、見(jiàn)解和信仰越來(lái)越明顯地受到視覺(jué)文化強(qiáng)有力的影響。”
但是,當(dāng)我們檢閱這些民間文化的影像資料時(shí),同樣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一些不可忽視的問(wèn)題,例如早期的影像作品大多質(zhì)量粗糙、簡(jiǎn)略,令觀看者對(duì)表述內(nèi)容不知所云;拍攝者的種族或文化偏見(jiàn),使得一些影像作品帶有強(qiáng)烈的歧視性“獵奇”色彩;創(chuàng)作者擺拍或作假,使得某些影像作品的真實(shí)性遭到質(zhì)疑;此外,意識(shí)形態(tài)或商業(yè)利益等因素,也會(huì)造成影像內(nèi)容的扭曲或誤導(dǎo),偏離了民間文化的真正價(jià)值。
在保護(hù)與傳承民間文化的影像工作中,我們不妨引入人類學(xué)的“影像民族志”概念與方法,或許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。所謂“影像民族志”,通常是指人類學(xué)者、民俗學(xué)者運(yùn)用影像拍攝的方法,記錄田野所見(jiàn)的社會(huì)行為或文化事象,再通過(guò)影像剪輯等后期制作手段,構(gòu)建以特定的社群文化為主題的影片內(nèi)容,創(chuàng)作出富于文化描述和理論闡釋價(jià)值的影像文本。在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生活中具有精神價(jià)值的民間文化,也是影像民族志所要記錄和表現(xiàn)的重要內(nèi)容。
人類學(xué)者通常以“田野調(diào)查”和“參與觀察”作為核心方法。“田野調(diào)查”是指在一個(gè)地區(qū)較長(zhǎng)時(shí)間的駐地生活與入戶調(diào)查,反對(duì)書齋式的研究,強(qiáng)調(diào)在社區(qū)生活和文化現(xiàn)場(chǎng)中獲得第一手資料;“參與觀察”則是指人類學(xué)者通過(guò)親身參與社群的各項(xiàng)活動(dòng):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、婚喪儀式、宗教信仰以及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和文化活動(dòng)等,以“準(zhǔn)內(nèi)部成員”的身份,體驗(yàn)、觀察和記錄其社會(huì)生活的主要內(nèi)容。作為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界最具實(shí)踐精神和人文關(guān)懷的學(xué)科之一,人類學(xué)原本就與民間文化的研究、保護(hù)有著密切的關(guān)聯(lián),當(dāng)以人類學(xué)為依托的影像民族志方法進(jìn)入到民間文化領(lǐng)域,便能夠?yàn)槊耖g文化的保護(hù)與傳承提供更為嚴(yán)謹(jǐn)、明晰的影像創(chuàng)作規(guī)范。
首先,影像民族志強(qiáng)調(diào)一種“互為主體性”的文化立場(chǎng)。所謂“互為主體性”,是指在影像創(chuàng)作者與民間文化持有者之間,不存在文化上的高低貴賤之分,而是要堅(jiān)持一種平等的、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本信念。由于城鄉(xiāng)差別、民族差異、經(jīng)濟(jì)水平、社會(huì)地位與教育程度的不同,外來(lái)的民間文化保護(hù)者往往擁有更為強(qiáng)大的話語(yǔ)權(quán)力,特別是在影像文化薄弱的地區(qū),掌握照相機(jī)、攝影機(jī)的人,似乎更具有某種身份上的優(yōu)勢(shì)。這也是我們經(jīng)常會(huì)在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或邊遠(yuǎn)山區(qū)所看到的,一群攝影師、攝像師圍著幾個(gè)不知所措的本地人肆意拍攝的景象。影像民族志工作者反對(duì)這種對(duì)影像權(quán)力的濫用,更反對(duì)將自身的文化意志凌駕于研究或拍攝對(duì)象之上,更不能通過(guò)擺拍、虛構(gòu)或拼湊素材等方法,炮制符合自身需求的影像文本。一部合格的影像民族志作品,是以對(duì)他者文化的承認(rèn)與尊重作為最基本的評(píng)判標(biāo)準(zhǔn)。因此,民間文化的影像保護(hù)也應(yīng)建立在“互為主體性”的基礎(chǔ)之上。
其次,在具體的影像拍攝過(guò)程中,影像民族志工作者應(yīng)遵循“社區(qū)合作”的原則,將拍攝目的、主題與方法和當(dāng)?shù)厝诉M(jìn)行協(xié)商、探討,邀請(qǐng)社區(qū)成員作為項(xiàng)目參與者,合作完成影像的攝制工作。影像民族志作者不應(yīng)無(wú)視社區(qū)的傳統(tǒng)文化習(xí)俗,在未經(jīng)許可的情形下拍攝某些帶有禁忌色彩的場(chǎng)景,更不能以影片“導(dǎo)演”自居,要求社區(qū)成員按照其拍攝要求進(jìn)行沒(méi)有事實(shí)依據(jù)的文化表演。“社區(qū)合作”原則的核心思想,是承認(rèn)并尊重研究與拍攝對(duì)象的“文化主權(quán)”,放棄居高臨下的自我文化中心主義,尋求后者以開(kāi)放的態(tài)度接納影像民族志作者的田野工作。惟其如此,民間文化的真實(shí)圖景,才有可能在合作拍攝的過(guò)程中展現(xiàn)出來(lái),并且被鄉(xiāng)村集鎮(zhèn)的社區(qū)成員——也就是文化的持有者們承認(rèn)與珍視。如果我們將民間文化的影像保護(hù)視作民間文化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(而非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務(wù)),就能夠更為透徹地理解“社區(qū)合作”原則在民間文化保護(hù)中的核心價(jià)值。
第三,在社區(qū)合作的基礎(chǔ)之上,影像民族志作者應(yīng)建立一種“影像分享”與“視聽(tīng)互惠”的拍攝關(guān)系。在影視人類學(xué)界對(duì)田野工作的反思中,“影像剝削”是一種常有的指責(zé),也就是學(xué)者或影像工作者單純地以自己的學(xué)術(shù)研究、影片創(chuàng)作為目的,在獲得足夠的田野資料或影像素材之后,便切斷了與信息提供者之間的聯(lián)系,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也無(wú)法惠及當(dāng)?shù)氐拿癖姟S跋衩褡逯玖D破除這種單向的信息流動(dòng)方式,由于影像本身所具有的視聽(tīng)功能以及直接、易懂的交流特性,尤其適合在拍攝者與被拍攝對(duì)象之間形成一種“影像分享”的關(guān)系,民間文化的持有者能夠在影像民族志的拍攝和剪輯過(guò)程中,隨時(shí)觀看、解讀并共享這些影像資源,影像民族志的主體素材和完成作品,也應(yīng)該在合作者當(dāng)中放映,并以拷貝形式留存給社區(qū)伙伴,作為社區(qū)自身保有的一筆文化財(cái)富。正如法國(guó)著名的人類學(xué)家、影像民族志工作者讓·魯什所言:“知識(shí)不再是一種遭竊取的秘密,被供奉在西方世界的知識(shí)廟宇里。它應(yīng)是民族志作者與他們的研究對(duì)象在‘分享人類學(xué)’的道路上相逢之后,所進(jìn)行的一種永無(wú)止境的探索。”
最后,在數(shù)字影像科技迅猛發(fā)展,影像器材高質(zhì)廉價(jià)的當(dāng)代,影像民族志工作者更鼓勵(lì)民間文化持有者學(xué)習(xí)、掌握影像創(chuàng)作技能,自主攝制民間文化主題的社區(qū)影像作品,與外來(lái)的文化保護(hù)者和研究者進(jìn)行雙向的影像交流,達(dá)成更趨近真實(shí)的文化共識(shí)。根據(jù)田野經(jīng)驗(yàn),即便外來(lái)的工作者如何以滿腔的誠(chéng)意來(lái)呈現(xiàn)、闡釋拍攝對(duì)象的文化事象,總會(huì)存在“主位”與“客位”之間的視角區(qū)別與認(rèn)知差異,而外來(lái)者主張的影片主旨和價(jià)值取向,往往無(wú)法滿足社區(qū)成員對(duì)自身文化的主觀評(píng)價(jià)。近十幾年來(lái),數(shù)字影像(通常被簡(jiǎn)稱為DV)的誕生與發(fā)展,第一次將高品質(zhì)的音畫質(zhì)量、靈活的拍攝與后期制作方式與相對(duì)低廉的產(chǎn)品價(jià)格聯(lián)系在一起,從而在物質(zhì)條件上為影像創(chuàng)作的主體轉(zhuǎn)換奠定了基礎(chǔ),讓始終處于“他者”地位的少數(shù)族裔、鄉(xiāng)村社區(qū)成員、城市普通民眾——也就是民間文化的主要傳承者——擁有了自主記錄、表達(dá)與傳播文化觀念的影像力量。
自2000年至今,從云南、青海、四川、貴州等多個(gè)具有示范性與延續(xù)性的社區(qū)影像項(xiàng)目可知:文化背景各異、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的農(nóng)牧民和手工藝者,經(jīng)過(guò)短期培訓(xùn)之后,都能夠掌握數(shù)碼影像的拍攝與編輯技能,也有能力以影像的方式表述其創(chuàng)作主題。視聽(tīng)語(yǔ)言所具有的直觀性、敘事性以及簡(jiǎn)潔的影像構(gòu)成語(yǔ)法,讓民間文化傳承者在創(chuàng)作影像作品時(shí),較之文字寫作,更易于表達(dá)他們的知識(shí)體系和思想觀念。從已經(jīng)完成且公映的多部村民影像作品中,我們能夠看到許多有別于主流價(jià)值與外部視角的民間文化觀念,它們以影像為載體,對(duì)本民族或本社區(qū)的鄉(xiāng)土知識(shí)進(jìn)行了“主位”立場(chǎng)的文化表述。這種影像創(chuàng)作不僅彌補(bǔ)了民間文化的知識(shí)圖景,也為民間文化傳承者提供了一種更為鮮活、自由的表達(dá)工具,讓“他者”的聲音真正被外界聽(tīng)到。
對(duì)于民間文化的研究、保護(hù)與傳承而言,影像民族志的啟示價(jià)值在于提供了一種相對(duì)系統(tǒng),兼具學(xué)術(shù)背景與實(shí)踐價(jià)值的工作方法。它所強(qiáng)調(diào)的“互為主體性”立場(chǎng)、“社區(qū)合作”原則、“影像分享與視聽(tīng)互惠”關(guān)系,以及對(duì)自主性社區(qū)影像的倡導(dǎo)和推動(dòng),都是當(dāng)代中國(guó)民間文化保護(hù)工作可以參考、運(yùn)用的基本方法。在影像元素?zé)o處不在、民間文化迅速流逝的當(dāng)代,影像民族志應(yīng)當(dāng)發(fā)揮更為積極的作用,成為中國(guó)民間文化工作者有效掌握、廣泛運(yùn)用的行動(dòng)工具。